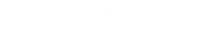曹禺|万方:灵魂的石头——纪念我的爸爸曹禺( 三 )
我们走上楼 , 楼梯更加暗了 , 又窄;记忆里楼上的光线像是亮堂一些 , 房子也比较宽敞 。
“那时候真是乌烟瘴气哟!哥哥在楼下抽 , 父亲母亲在楼上大客厅里抽 。 那间大客厅 , 北洋军阀的大政客黄郛来过 , 黎元洪的姨太太也来过 , 真奇怪 , 过去的事情竟然记得这么清楚……”
我爸爸一次又一次站住 , 四下张望 , 置身于他的童年之乡 , 实在使他迷惑不解 。 我则想像出一个不大的男孩儿 , 放学回家时的情景 。 家里十分安静 , 没有人声 , 空气中飘散着一股他熟悉的气味 。 他走进自己的屋子 , 做自己的事儿 , 但是有一种东西一点点渗透到他的身体里面 。
站在阳台上 , 他指给我看王傻子的家 。 王傻子就是那个陪他念书的书童 , 不用交钱 , 送两袋棒子面儿给老师 。 “我们一块儿在院子里演戏 , 文戏武戏都演 。 我和他一起乘电车看无声电影 , 是《马瑞匹克弗》 , 在光明电影院 。 ”
后来我们下了楼 , 经过一间屋子 , 他说那是他们吃饭的地方 。 “我最怕吃饭 , 父亲总是在吃饭的时候发脾气 , 骂厨子 , 有一次一脚就把哥哥的腿踢断了 。 ”他沉默了一会儿 , “我父亲 , 他高兴时就背我 , 我十五岁时 , 他还背过我 , 在屋里走啊走啊 。 ”
我们在小白楼前照了相 , 我爸爸指着街道旁的空地 , “就在这地方 , 排着一溜人力车 , 天津人叫‘胶皮’ , 不问价钱 , 上去就走 。”他又指着一座临近的小楼 , “这就是周金子的家 。 周金子是个妓女 , 我忘记了是什么阔老爷花了一万块钱 , 把她买来做姨太太 。 这座小洋楼就是专门为她盖的 。 为什么叫金子?一万块钱 , 太贵重了 , 像金子一样 。 ”他说那时他特别想看看周金子的模样 , 可她不大出来 , 偶尔在夏天 , 洗了澡出来一下 , 只是在阳台上一晃 , 在他少年的眼睛里 , 他觉得她长得很美 , 像神仙似的 。
他记得在胡同口经常看到逃难的农民 , 一头挑着锅 , 一头挑着孩子 , 晚上叫得很惨 。
这是我陪我爸爸回天津旧居时的大致情景 , 我想说的是我有一种感想 , 出生在旧中国的文人 , 他们大多从小就感到压抑 , 继而觉悟到有一股与他们格格不入的势力的存在 , 从此他们的生存就处于个人与一种势力对峙的状态 。 这成为他们无法逃脱的命运 , 他们也不想逃脱 , 他们从来无缘体味“为艺术而艺术”的闲情逸致 , 这才是他们的情结 。
我爸爸写剧本就是他的作为 。 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 , 才华更是上天给的 。 我爸爸有幸被赋予了才华 , 他的成名是在很年轻的时候 , 像几乎所有当代的中国文人一样 , 在二十几岁就迸射出生命中创造的光辉 。 我体会他真正的才华 , 在于他全身心地活在自己独特的感觉之中 , 登上了自己的那块石头 。 他迎接命运 , 他愤愤不平 , 他痛苦 , 他要反抗 , 一股股激流从他身边汹涌而过 , 他的心被激荡 , 也许他也想化为激流 , 或者说把自己投身进一股强大的力量里 , 可在他的心灵中有一个小人儿 , 具有把握他的更大的力量 。 就由于有他的把握 , 他写出《雷雨》 。
那时他还在南开中学念书 , 有一个同学叫杨善全 , 他和杨善全说 , 我有一个故事想写出来 。 这位同学就说 , 那你讲讲吧 。 他说:“我讲了 , 讲得乱七八糟 , 他也没听出所以然 , 只说 , 很复杂呀 , 你写吧 。 ”
“你们要我讲繁漪是从哪儿来的 , 有什么原型?有 , 肯定是有 , 好多好多 。 但要我说出张家老太太 , 李家少奶奶 , 王家小姐 , 有什么用?讲了也是白讲 , 你们也不认识 。 《雷雨》这个名字 , 如果硬要我讲 , 雷 , 是轰轰隆隆的巨大声音 , 惊醒他们;雨 , 是天上而来的洪水 , 把大地洗刷干净 。 ”这番话是和来采访他的人说的 。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爱情 爱是灵魂深处最美的懂得
- 罗子君|异性相处,有了这三种感觉,才算是真正的灵魂伴侣
- 李白|成为男人的“灵魂伴侣”,是需要套路的
- “我将于人海茫茫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 徐志摩和陆小曼:一个是有妇之夫,一个是已婚女人
- 网易 窗外的人生,窗内的灵魂
- |灵魂知己,是生命中最美的情缘!
- 一个灵魂高尚的人必须有一颗平静的心。
- 灵魂高贵之人,心中必有一份静气
- 年末灵魂拷问:你的拖延症治好了吗?
- |讨骂专栏:男人会爱上女人的灵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