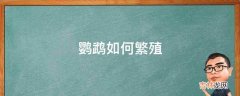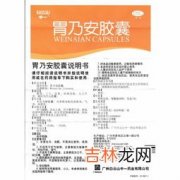离婚|离婚骤减5成,是政策“抬高门槛”还是上辈“垂帘听政”?|文化纵横( 四 )
当然这只在推理意义上成立 , 现实的婚姻实践中一个30天的“冷静期”措施 , 并不能给整个社会的婚姻走向带来多大影响 。 之所以说中国目前不太可能走向西方所谓的“单身社会” ,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 , 对于中国人而言 , 婚姻总体上还是一个红利或者被视为一个对多数人利好的特权制度 , 尤其是相对于那些还在为同居者权利而争取、为单身女性生育权而呼吁、为同性婚姻合法化而努力的人群来说 , 这是不争的事实 。 尽管婚姻的脆弱性已经提示人们 , 家庭不一定是充满凝聚力和温情的安全港湾 , 然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 , 家庭又何尝不是那份最不可或缺而又唯一不设准入门槛的宝藏级资源?尤其在国家的社会保障支持力度尚不足以满足个体生命历程的需求、政府将越来越多的责任和负担下沉到家庭的制度背景下 , 婚姻成为助益个体获取福利支撑的重要渠道和工具 , 由此婚姻的私人性也在不断扩张中完成了其公共性的社会输出 。 因此也可以说 , 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博弈造就了纷繁复杂的婚姻和家庭实践形态 , 谁都不能置之度外 。 而关于离婚干预的制度调整 , 只不过是新时期开启的又一轮协商的试探 。
▍焦点三:“前浪”与“后浪”的话语权之争?
在关于“冷静期”的争论中 , 来自反对者的最尖锐意见 , 其实并非离婚干预是否限制了离婚自由 , 而在于协议离婚背后关于“冲动”和“冷静”的假设 , 被网民认为是以长辈为主体的立法者针对年轻人设置的充满父爱主义的、“爹味十足”的法条 。 这种词汇和叙述方式像极了中国家庭内部常常出现的场景:父母以过来人的身份、打着“为你好”的旗号逼迫子女以他们安排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事———立法者在此似乎充当了人们熟悉的家长形象 , 所谓“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 这些网络上流行的“梗”充分反映了“后浪”对于“前浪”以爱之名义控制和压迫的反感 , 也体现了当下社会和文化中代际冲突的普遍性 。 因此也有人将这次“冷静期”的争议描述为“前浪”与“后浪”之间的话语权之争 。
从世界范围内看 , 代沟和代际冲突早已成为20世纪以来最令人瞩目的主题之一 , 原因在于社会变迁的剧烈导致知识和价值观在不同代之间的迅速分化和多元化 。 断代的时间越来越短 , 从几十年、十年 , 到如今恨不得不足五年就算一代 , 以致用“××后”这样的出生年代划分都已经不够用了 , 这是因为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的数字鸿沟加速了代际分化 , 同时也形成了思想和文化上多元主义和部落主义的盛行 。 权威的消解不仅仅是当下社会价值观的常态 , 也是变迁中的家庭面临的一个困境 。 许多家庭研究学者发现 , 中国在市场化转型之后出现的家庭变革似乎很难完全用单一的西方经典家庭理论得到诠释 , 因而在家庭的核心化、平等化、个体化之外 , 也出现了家庭的网络化、流动性、杂糅性等新的叙述方式 。 其中关于代际和亲子关系特征的描述最为吊诡 , 由传统的反馈或接力的二元模式 , 替换为向下倾斜的“协商式亲密关系” 。 这种被阎云翔称为“下行式家庭主义”或者“新家庭主义”的共同体模式 , 描绘了中国家庭在应对社会转型压力时所呈现的代际关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一方面是风险共担下的亲权回归和代际亲密互动;另一方面又在协商中小心翼翼地护卫着个体的自主性免受伤害 。 这表明“前浪”与“后浪”在私人生活中的立场并非总是冲突的 , 他们也是“相爱相杀”的队友甚至共谋者 。
因此 , 有关“冷静期”的争议 , 与其说是“前浪”与“后浪”的话语权之争 , 不如说是对婚姻中权力关系的不同理解和期待 。 面对婚姻中出现的问题 , 当事者双方并非一定具有同等的讨价还价能力 , 离婚与否给双方带来的预期也不尽相同 。 因此 , 作为协议离婚基础的协商 , 很多时候可能并非彼此真正达成了共识 , 只不过是弱势一方放弃了自己本应有的权利和利益换来的“止损”行为 。 这也正是一些法学界人士担心协议离婚流程太过简易有可能造成显失公平的结果 , 因而建议采纳“冷静期”作为缓冲设置的初衷之一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增设一个月的时间门槛不如理解为一种“试离婚”的预警 , 这一流程虽说并未打破由当事者自主约定的协商性质 , 但由于加上了政府给定的时间门槛这个第三方砝码 , 却有可能重建婚姻关系谈判中微妙的权力平衡 , 因为它等于给婚姻的解除增设了一个30天的“倒计时” 。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离婚|女人离婚后生活怎么办?这个女人讲了真心话
- 林庆昆|《完美伴侣》“离婚了,我就没有家了!”林庆坤为何是这个反应?
- 01我和鹏是在朋友聚会上认识的 我以为我是个不讨喜的女人,也更加坚定了离婚的决心
- |认识3个月,交往1个月结婚,6个月后就办了离婚,女人:早料到了
- 汪小菲|汪小菲离婚后首次采访:比以前更敢说更开心了,整个人变帅不少
- 离婚 老公出轨,女人最好的选择是什么?这个姑娘的案例告诉你
- 陆斌 千万家产包租公离婚后,在前妻的介绍下,把女租户发展成陪睡保姆
- 养老|女婿,我老了,我命令你给我养老,要不我就要你离婚!女婿:行
- 张靓颖|张靓颖:在父母离婚阴影中长大,失婚后情感状况怎么样?
- 杨可可|去领离婚证的路上出了一场意外,我和老公永远也离不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