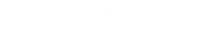我的南行凭籍的不是什么豪迈的胆气 , 而是抑制不住的浪漫情怀 , 像野草一样只需一缕东风吹拂 , 便开始萌动 , 疯长起来 , 遮蔽了前路坎坷的真相 。 我迫不及待 , 憧憬着南方的椰林、香蕉林、珠玑巷、树皮小屋、朱雀玄鸟…… 。 我的爱不再拘泥于华中那个小山村和让我无从安顿自己的故城 , 我将在南方的天底下辗转流离 , 让生活的琐碎将自己瘗埋 。 在不徐不疾的绿皮火车上(现在从家乡到深圳坐高铁只需四个半小时 , 但那时绿皮火车之旅长达三十个小时) , 我领教了身体超强的承受能力 , 在漫长的颠踬中 , 追逐着各自梦想的人们挤在一起喘息、渥汗 , 因为饥饿和极度的疲惫 , 屡屡突破男女授受不亲的樊篱 。 但决不是淳于髡所说的握手无罚 , 目眙不禁 , 更无关于罗襦襟解和微闻芗泽 。 只有现实的窘迫消融了陌生的羞怯和禁忌 。

本文图片
多年以后回首往事 , 才惊觉自己曾经患上了不谙世事的幼稚病 。 如果不是深入南方的肌理 , 我对她的认识便仅限于传闻 , 无从看清她虽然张开着双臂 , 却审慎地避开寻梦者一厢情愿的热情 , 因为她一时还无从适应汹涌而来的人潮 , 于是 , 伴随着打工潮衍生出许多新事物:暂住证、“三无”、盲流、打工仔、外来妹、遣返……
无一技傍身 , 惶惑被梦想暂时蒙蔽 。 那种惶惑让我想到了一个人 , 约莫二百年前 , 丹麦有一个出身贫苦的小镇少年 , 想凭着并不出色的歌唱天赋当上歌唱家 , 他一头扎进哥本哈根 。 在肾上腺素快速上升的时刻 , 初生之犊闯进皇家剧院经理家里 , 对方冰凉的冷漠中混合着高浓度的傲慢 , 在单薄的少年面前 , 他强忍不悦说 , 好吧 , 你唱给我听听 。 少年使出了浑身解数唱起来 , 然而 , 命运诸神并没有在那个节骨眼上统一意见 , 让他顺利过关 , 而是对他另有安排 , 让他走上了另一条羊肠小径 , 并最终赋予那个名字不凡的意义 , 他就是安徒生 。 如果安徒生侥幸当上了歌唱家 , 就不会有拇指姑娘和丑小鸭 , 也不会有皇帝的新装 。 但想到了安徒生什么也说明不了 , 我不是安徒生 。
也许 , 蚀骨的惶惑是成长的有益养料 。 当然我一定要提醒自己:在这颗卓荦不群的蓝色星球上 , 从生物意义上来说 , 痛苦只是基因传递的副产品 。 至于基因传递的终极意义是什么 , 现在还远远不是能够揭橥的时候 。 我一个后来当上了教授的朋友当时就说过 , 对有的人来说 , 再多的痛苦也是徒然的 。 不过即使如此 , 我还是觉得 , 一切众生皆是肩负某个神秘使命的使者 。
以梦为马的少年啊 , 怎能忘了那时的马瘦毛长!
还记得 , 空空的行囊里有一个文件袋 , 夹着我见诸报端的“豆腐块” , 窃以为到了阳光明媚的南方 , 情急之下或许能当敲门砖幸运地敲开某一扇门 。 它们差不多是我唯一引以为傲的东西 , 然而 , 在颠沛流离中它们从来都没有派上用场 , 最后如泫露一样消失了 。 那是我一生中最容易从唐·吉诃德的命运里看到自己影子的日子 , 以乐观和豪情为武器 , 除了屡屡与虚拟的敌人作战也与另一股敌人作战 , 它们是懦弱、倦怠、失望、自卑、消沉……操着各样的武器向我张牙舞爪地扑上来 。
东莞长安——既是我的洼地也是我的福地 。 在一头扎进南方的初年 , 我曾经用绵密的足迹丈量过它 , 并憧憬着自己的足迹是广种薄收的种子 , 能在此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 卢梭说过 , 上帝只关注物种而忽略个体 。 如果衪也关注一切众生的每个小小愿望 , 大概就不会让数不胜数的榕树果徒然舛落 , 也不会对天灾人祸视若无睹 。 踏上燠热的南方 , 有人善意地劝阻我 , 这儿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 。 言毕还伴随着摇头和叹息 , 无形中加重了劝阻的力度 。 虽然穷猿奔林 , 但转念一想 , 如果热火朝天的南方都不是我的安身之地 , 那么哪儿才是我的立命之所?在强者与弱者并存的地方 , 为什么偏偏只有我待不下去?这显然不是一个逻辑可以自洽的问题 。 打击我的力量也滋养着我 , 现在我肩负着一个使命:要把别人的南方变成自己的南方 。 正如我的祖先 , 很久以前失去草原和马匹 , 却收获了南方延绵的群山 。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悦读|晚间悦读丨遇事不争论,遇难不回避,遇错不责人
- 爱情|itotii心语丨别再留恋了
- 散文|散文|李龙宇:真为你高兴
- |夜读丨一个人的教养,藏在这4种细节里
- |夜雨丨张刚:改变
- 毛泽东|诗词丨开一扇晴窗,迎一米阳光
- |援吉林抗疫日记丨出院患者越来越多 期待人间皆安
- |微视频丨英雄归来
- |夜读丨成年人最了不起的能力:扛得起事,稳得住心
- 本文转自:上游新闻“社交恐惧症已经有点影响到我的工作和生活了……”近日 上游帮忙丨“社交恐惧”让她丢了工作?心理学教授教你三步反“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