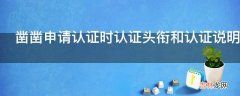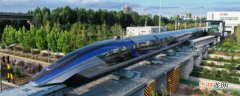尽管已经接受了丈夫离开的事实 , 但伤痛依然尖锐 , 折磨着我 。
我的脑海 , 时常不受控制地浮现出医院里的场景 。 看电视一看到流血 , 就极为痛苦 。
我的记性也大不如前了 , 经常丢三落四 , 坐车回家竟然提早一站下了车 。 我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 , 觉得一切没有意义 , 好像连笑都不会了 。 人始终处在一种紧绷的状态 , 不能放松下来 。
我还变得暴躁易怒 。 听见跟他有关的、能联想起来的话题和词汇 , 就会紧张 , 甚至喘不上气 , 想立马逃离那个环境 。
在这种状况下 , 我切断和他有关的一切联系 , 与我原来的朋友圈也断开了 。 尤其是关系要好的共同朋友 , 更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
我是后来才知道我病了 。 而这些症状难以描述 , 也无法量化 。 于是 , 在挣扎了八个月之后 , 我鼓起勇气寻求医生的帮助 。 2021 年国庆节假期前夕 , 我来到北京 , 在一家心理救援机构接受医生的治疗 。
这是我第一次做心理咨询 , 内心有些忐忑 。 医生是国内知名的心理救援、危机干预专家 , 坐在他面前 , 我发现他态度很和蔼 。 他很耐心地和我聊天 , 问我问题 , 详细记录我的情况 。 最终 , 他给出诊断 , 我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
但是医生说 , 因为我此前的生活经历和原生家庭都很健康 , 没有掺杂其他更复杂的内容 , 这就有益于后期的治疗和恢复 。
也是通过这次机会 , 我发现 , 心理咨询并不完全是我想象中的那样 。 它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 而是要问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 , 问清我的成长经历和原生家庭状况 。
一个小时的咨询很快结束 。 最后 , 医生还给了我两点建议 , 「走路和写日记」 。

本文图片
小蒋的病历本 。
图源:受访者供图
除了医生 , 我的家人们也在帮助我 。
我的父母年岁渐长 , 本是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 , 却因我的遭遇 , 让他们一起承受了痛苦 。 这一年母亲因为担心我 , 生出了好多白发 。
我记得去年国庆节前夕 , 在去北京的路上 , 高铁疾驰而过 , 窗外景物依然 , 我却高兴不起来 。 晚高峰 , 北京西站格外拥堵 , 在北京生活的表妹却坚持到车站接我 。 整个国庆假期 , 舅舅也处处考虑我 , 问我「想吃什么 , 想去哪里玩」 。
我知道对我而言 , 失去丈夫的哀伤只能独自咀嚼消化 , 旁人能给的建议十分有限 。 更多时候 , 家人们是在陪伴、倾听 , 但这也是一种帮助 , 并且弥足珍贵 。
我什么时候能彻底恢复?我不知道 。 未来 , 我还需要数次的心理干预治疗 。
回顾这段日子 , 我觉得至亲意外离世 , 心理干预必须越早越好 。 尽管每个人面对这种情况 , 反应会不尽相同 , 但一定会感到悲伤 。 如果刻意压抑悲伤 , 装作若无其事 , 反而容易酿就更大的问题 。
我知道未来一段时间 , 我还会痛苦、低落 , 但我尝试把这件事看作人生的一个低谷 。 尽管若干年后 , 这件事情在我心里 , 也一定会是一道抹不掉的伤疤 。
但我知道我能恢复过来 。 会有那么一天 。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 , 文中小蒋为化名 。 )
撰文:小蒋
监制:潘闻博
【丈夫|丈夫去世1年,确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我,在努力消解丧亲之痛】首图来源:站酷海洛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董竹君|董竹君:连生4女被丈夫追砍,父母的笑,成压垮她婚姻的最后引线
- 冯晓琴|嫁到上海人家,丈夫让她辞职做了全职太太,她要的不是房子本身
- 离婚 丈夫去快递站替妻拿包裹,当场拆开见是情趣用品,觉得丢人要离婚
- 青花 老农挖到一瓷器,拒20万收购上交国家,11年后专家为何上门道歉?
- 保大人|纪实:妻子怀孕8月患癌,医生问保大人还是小孩,丈夫:一个不要
- 去世指南|“妈妈,你死了我怎么办”妈妈写了一份《去世指南》,温暖所有人
- 外卖员 外卖员凌晨送餐被打死,妻子发声:丈夫性情温和,要求严惩凶手
- |好的丈夫,才配有好的妻子!说的太有道理了
- 妻子出轨后对丈夫挑衅“有本事你杀了我”,丈夫捅死妻子如何判刑
- 高秀敏女儿李萱:父母相继去世,公婆给我爱,你是我们第二个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