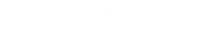手术过程 , 仅打了腰部麻药 , 但我几乎都是清醒的 。 那种刺骨、钻心的痛 , 让我整个人都麻木了 。 不过还算坚强 , 没有哭闹 。 三次手术 , 有一次失败了 , 前后加起来住院大半年 。
回家后 , 我腹部以下打了石膏 , 不能站立、蹲坐 , 只能平躺在床上 , 像一具木乃伊 。
那一段时间 , 我每天躺在床上看书、睡觉 , 醒来又看书 。 我记得 , 看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时 , 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了一句:这样的书我也写得出来 。
拆掉石膏后 , 经过大约一年时间的休息和康复训练 , 身体才慢慢恢复正常 。
两年后 , 我去中学报名 , 校方说我的学籍没有保留 , 没有资格入学 。 从此失学 。
此后 , 我经常给街道上的泥木工打下手 , 去火车南站推板车 , 藉此挣点小钱 , 也算锻炼身体 。 喜欢一个人坐在家门口的麻石台阶上发呆 , 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干什么 。
以前 , 父亲在工厂上班 , 一个星期回来一次 , 每月工资五十几块钱 。 除了给家里的生活费 , 他自己会留几块钱抽烟、喝酒 。 年轻的时候他过了一段时间的优越生活 , 上过大学 , 会唱英文歌、吹口琴 , 写得一手漂亮的字 。

本文图片
父母于1937年在青岛结婚 。
但父亲一辈子不得志 , 晚年大部分时间一个人躲在房间喝酒 。
他是统计学专业的学生 , 对数字有种天生的热爱 。 哪怕后来潦倒不堪 , 仍喜次记账 。 他的账簿里 , 金额最少为一分钱(两担自来水) , 次之两分钱(一盒火柴) , 最多至五十四块五(每月工资) 。 每次买回一盒火柴 , 他必定要数火柴根数 , 并记在账本上备注:上次一盒总计九十五根 , 此次一盒总计九十一根 , 少四根也 。
上世纪六十年代 , 父亲制定了一家人用粮计划安排表 , 将全家每人每日安排的用粮数精确到两、钱、分、厘、毫 , 比如我二哥每日的平均用粮数为13.9354两 。

本文图片
1961年苦日子时期 , 父亲为家庭成员手绘的用粮计划安排表 。 每人每天口粮之计量单位细分至“两、钱、分、厘、毫” 。
所以那时候我好奇地问过父亲 , 一粒米到底有多重?
父亲似有些难堪 , 但也告诉了我一种方法:先数出一百粒米或者一千粒米 , 称出它们的重量 , 再除以一百或者一千 。 我至今也没有算过 。
五十年一觉文学梦
十九岁时 , 我认识了五十多岁的诗人彭燕郊 , 并和他成为了忘年之交 。
那时候 , 彭燕郊在长沙北区阀门厂做油漆工 。 我去工厂找他 , 他把手套脱了 , 我们偷偷地聊小说、诗歌 , 以及梦想 。 有的时候 , 我去他湖南省博物馆的家(他妻子在湖南省博物馆上班) , 一聊好几个小时 , 偶尔也在他家里吃饭 。
我在他家用手摇唱机听黑胶唱片 , 读波德莱尔的《恶之花》 , 以及美国“嚎叫派”诗歌 , 欣赏俄罗斯的绘画作品……尽管多是从画报上剪下来的 , 但我依然觉得很新鲜 。
每天 , 彭燕郊从家里到工厂上班 , 坐公共汽车要经过南门口 。 隔一段时间 , 他会在南门口下车 , 走到“倒脱靴”10号公馆 , 给我送来新书 , 并把之前借给我的旧书拿回去, 恍若地下工作者交换情报 。
那个年代 , 我的两个姐姐、一个哥哥 , 下乡当了知青 。 因为身体不好 , 我留在长沙 。 一开始 , 我进了长沙机床厂 , 成为了一名合同工 , 负责起吊机床部件 , 几乎没有技术含量 。 对于我来说 , 彭燕郊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书本 , 更是对未来的希望 。 1978年 , 恢复高考后 , 很多知青参加高考 , 考上了大学 。 我只有小学毕业 , 没有办法参加高考 , 于是一个人偷偷地写作 。 写的多数是那些困惑、悲伤的生活 。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姚笑梅|“作家新干线·散文”姚笑梅|住进月亮里的思念
- 潘向黎|暌违12年后鲁奖作家潘向黎推出新作《上海爱情浮世绘》洞悉世情
- 作家的包袱,扔了会怎样
- 作家佑子黄幼中《弟弟的麦田》散文诗集《木棉花开》第74篇
- 品读 | 有质量的日子
- 专访“熊猫作家”蒋林:要写出中国自己的“功夫熊猫”故事
- 范振彪:故乡月明|中原作家
- 李冬丽:明月与我长怀念|中原作家
- 作家蒙田这样说过:“美满的婚姻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之一 有时候,真的会感觉结错婚,比一辈子不结婚更可怕
- 一切都会重生|青年作家金鸿新书《一切都会重生》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与自我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