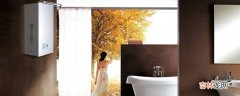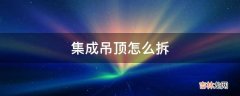本文转自:安徽日报扫码阅读更多内容一这条河的名字是我听过的世界上最好听的河流的名字——栀...|栀子河边,一灯如豆( 二 )
其实那时候我根本不认识字 。 大哥有时教我 , 我们兄弟姊妹们也比赛着背诵 。 这在村庄上是十分难得的 。 到我七岁时 , 我已经能背诵一些古诗了 。 虽然并不太懂其中的意思 , 但也学会了摇头晃脑 , 感觉仿佛也沉入了古诗的意境之中 。 或许 , 那种感觉是真实的 。 诗歌这种人类共同的文字 , 借着一豆灯光和轻声吟哦 , 进入亘古相传的情感之中了 。
栀子河日夜流淌 。 我也想跟村子里的孩子们一样上学 。 可是我年龄没到 , 那时候上学要等到八周岁 。 我吵着要去上学 。 父亲只好带着我过了栀子河 , 到大队小学 。 校长是父亲的老熟人 , 说孩子太小 , 且个子矮 , 上不了学 。 明年再来吧 。 我哭着要上学 。 校长便说:“你识字吗?会数数吗?”我说:“我会背诗 。 ”
没等校长同意 , 我就背开了 。 背完“云淡风轻近午天” , 我又背“春眠不觉晓”;校长眯着眼 , 看我还要背 , 赶紧摆摆手 , 说:“别背了 。 明天来上学吧!”
我上小学的第五年 , 正逢特大干旱 。 村子里都没水了 , 这时候 , 栀子河发挥了巨大作用 。 每家都在河里面挖深坑 。 地底下的水会冒上来 , 一开始 , 一个管一家人吃的水坑 , 一夜就能满水 。 但后来随着干旱的严重 , 水坑越来越浅 。 家里的用水也越来越紧张 。 我们四个男孩子会共用一盆洗脸水 , 这还算好的 。 很多家庭干脆不洗脸了 。 大人们白天干农活 , 晚上就抱一床席子睡在水坑边上 。 有人偷水 , 不得不防 。 那年 , 直到国庆后才开始下雨 。 瓢泼似的大雨打在干裂的土地上 , 冒出“哧溜”的青烟 。 大人接着雨水 , 疲惫的眼神 , 这时才又重新明亮 。
栀子河很快丰满起来 。 孩子们在河边上捞鱼 。 农田里 , 午季作物也开始下种了 。
三
栀子河流水不断 , 同样 , 一灯如豆之光下 , 读书之声也从来没有断过 。
灯换了 。 原来的油灯变成了电灯 。 当听说我们村子里要架电时 , 全村都沸腾了 。 人们晚上聚在一块儿 , 说得最多的就是电 。 有人问父亲:“电怎么就在玻璃里点着了呢?”
父亲也答不上来 。 倒是已经读高中的大哥给了回答:“电灯里有钨丝 , 通上电后 , 钨丝就会发光 。 ”
村里人自然不甚明了 。 但这回答已经够了 。 因为很快电线杆子就跨过栀子河 , 竖到了我们村子里头 。 家家户户也都开始安装电线 。 快过年时 , 上面通知说:“送电了 。 ”村庄里的人那天晚上都守在堂屋电灯下 。 忽然 , 灯泡发出明亮的光 , 整个屋子都亮了 。 亚先生也捻着白胡子 , 看着电灯 , 说:“这新鲜 。 新鲜 。 ”他伸手一拉闸线 , 屋子里漆黑 。 大家嚷着:“快开了 , 快亮起来 。 ”亚先生又一拉闸线 , 光明又来了 。 所有人的脸上都是笑 。 这笑比田里的稻子黄熟了还灿烂 , 比坡地上红高梁还鲜艳 。
在电灯下读书 , 一开始感觉还是有些怪怪的 。 从小习惯了在一豆油灯下看书写字 , 这乍一明亮 , 眼睛和心里都适应不了 。 有时 , 我会抬头看着灯泡 , 想像那灯光里是不是也有油灯样的灯芯 。 或者那里面有一个会发光的小人儿 , 就像夏夜的萤火虫 , 自己举着灯盏 , 满世界为别人照耀 。 渐渐地 , 适应了 , 一大家子人 , 会围坐在堂屋里 , 听父亲讲“士甘焚死不公侯”的介之推 , 讲“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 , 报刘之日短也”的陈密 , 讲“落霞与孤鹜齐飞 , 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王勃 , 也讲村子里从前的一些故事 。 特别是那些鬼故事 , 活灵活现 , 听着心里怕 , 却顽强地想听 。 晚上睡在床上 , 必朝里面墙壁 , 好像如此就能躲开那些父亲故事里的鬼魂 。
经验总结扩展阅读
- 冠军|委内瑞拉总统指责美国操纵环球小姐比赛,“他们抢走我们的冠军”
- 本文转自:南宁晚报旅客带上回家的礼物 带上年礼和心意回家啰!
- 本文转自:今晚报很多老人到了一定年纪 遗嘱咨询师 帮老人做好人生抉择
- 本文转自:光明日报光明图片/视觉中国腊月在一年的年底 腊月·故乡
- 本文转自:曲靖日报程刚我们村子不大 六叔的菜园子
- 星座|这三大星座爱的执着,分的干脆!
- 双子座|和双子座谈恋爱,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 学历|有文化,到底什么算是有文化?
- 本文转自:合肥日报春运大幕已经拉开不管您是已经到家还是正在回家的路上又或者是跟小编一样还...|@合肥人:说出您的2023春节故事,赢取500元现金奖励
- 本文转自:太原晚报护理员武连香和曹成让老人在一起。|坚守岗位陪老人过年